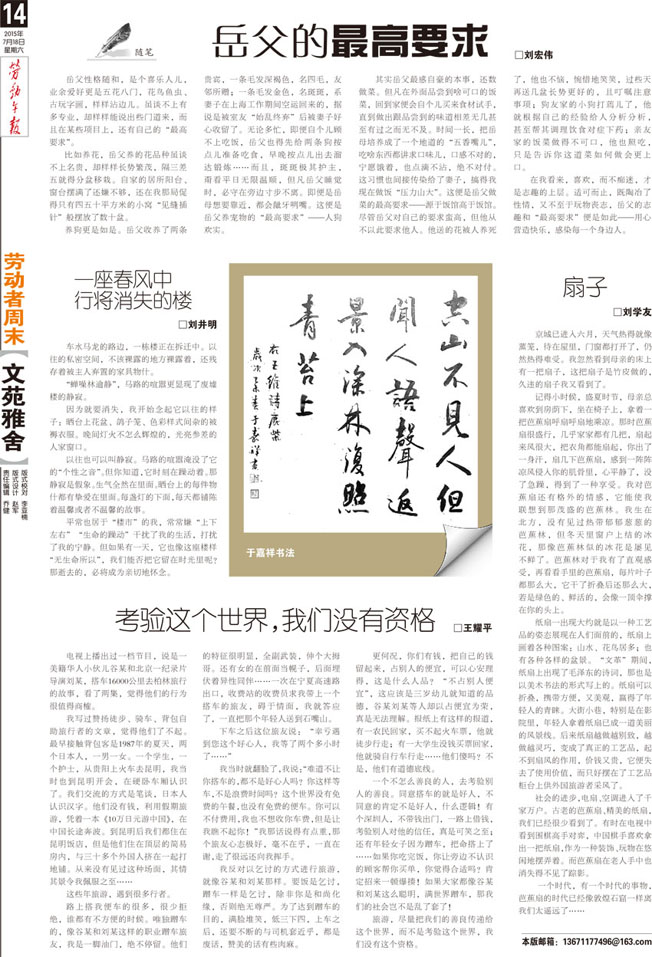文苑雅舍
2015-07-18
作者:
来源:
岳父的最高要求
□刘宏伟
岳父性格随和,是个喜乐人儿,业余爱好更是五花八门,花鸟鱼虫、古玩字画,样样沾边儿。虽谈不上有多专业,却样样能说出些门道来,而且在某些项目上,还有自己的“最高要求”。
比如养花,岳父养的花品种虽谈不上名贵,却样样长势繁茂,隔三差五就得分盆移栽。自家的居所阳台、窗台摆满了还嫌不够,还在我那局促得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小窝“见缝插针”般摆放了数十盆。
养狗更是如是。岳父收养了两条贵宾,一条毛发深褐色,名四毛,友邻所赠;一条毛发金色,名斑斑,系妻子在上海工作期间空运回来的,据说是被室友“始乱终弃”后被妻子好心收留了。无论多忙,即便自个儿顾不上吃饭,岳父也得先给两条狗按点儿准备吃食,早晚按点儿出去溜达锻炼……而且,斑斑极其护主,甭看平日无限温顺,但凡岳父睡觉时,必守在旁边寸步不离。即便是岳母想要靠近,都会龇牙咧嘴。这便是岳父养宠物的“最高要求”——人狗欢实。
其实岳父最感自豪的本事,还数做菜。但凡在外面品尝到啥可口的饭菜,回到家便会自个儿买来食材试手,直到做出跟品尝到的味道相差无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时间一长,把岳母培养成了一个地道的“五香嘴儿”,吃啥东西都讲求口味儿,口感不对的,宁愿饿着,也点滴不沾,绝不对付。这习惯也间接传染给了妻子,搞得我现在做饭“压力山大”。这便是岳父做菜的最高要求——源于饭馆高于饭馆。
尽管岳父对自己的要求蛮高,但他从不以此要求他人。他送的花被人养死了,他也不恼,惋惜地笑笑,过些天再送几盆长势更好的,且叮嘱注意事项;狗友家的小狗打蔫儿了,他就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人分析分析,甚至帮其调理饮食对症下药;亲友家的饭菜做得不可口,他也照吃,只是告诉你这道菜如何做会更上口。
在我看来,喜欢,而不痴迷,才是志趣的上层。适可而止,既陶冶了性情,又不至于玩物丧志,岳父的志趣和“最高要求”便是如此——用心营造快乐,感染每一个身边人。
一座春风中
行将消失的楼
□刘井明
车水马龙的路边,一栋楼正在拆迁中。以往的私密空间,不该裸露的地方裸露着,还残存着被主人弃置的家具物什。
“蝉噪林逾静”,马路的喧嚣更显现了废墟楼的静寂。
因为就要消失,我开始念起它以往的样子:晒台上花盆、鸽子笼、色彩样式间杂的被褥衣服。晚间灯火不怎么辉煌的,光亮参差的人家窗口。
以往也可以叫静寂。马路的喧嚣淹没了它的“个性之音”。但你知道,它时刻在躁动着。那静寂是假象。生气全然在里面。晒台上的每件物什都有挚爱在里面。每盏灯的下面,每天都铺陈着温馨或者不温馨的故事。
平常也居于“楼市”的我,常常嫌“上下左右”“生命的躁动”干扰了我的生活,打扰了我的宁静。但如果有一天,它也像这座楼样“无生命所以”,我们能否把它留在时光里呢?那逝去的,必将成为亲切地怀念。
考验这个世界,我们没有资格
□王耀平
电视上播出过一档节目,说是一美籍华人小伙儿谷某和北京一纪录片导演刘某,搭车16000公里去柏林旅行的故事,看了两集,觉得他们的行为很值得商榷。
我写过赞扬徒步、骑车、背包自助旅行者的文章,觉得他们了不起。最早接触背包客是1987年的夏天,两个日本人,一男一女。一个学生,一个护士,从贵阳上火车去昆明,我当时也到昆明开会,在硬卧车厢认识了。我们交流的方式是笔谈,日本人认识汉字。他们没有钱,利用假期旅游,凭着一本《10万日元游中国》,在中国长途奔波。到昆明后我们都住在昆明饭店,但是他们住在顶层的简易房内,与三十多个外国人挤在一起打地铺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,其情其景令我佩服之至……
这些年旅游,遇到很多行者。
路上搭我便车的很多,很少拒绝,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。唯独蹭车的,像谷某和刘某这样的职业蹭车旅友,我是一脚油门,绝不停留。他们的特征很明显,全副武装,伸个大拇哥。还有女的在前面当幌子,后面埋伏着异性同伴……一次在宁夏高速路出口,收费站的收费员求我带上一个搭车的旅友,碍于情面,我就答应了,一直把那个年轻人送到石嘴山。
下车之后这位旅友说:“幸亏遇到您这个好心人,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了……”
我当时就翻脸了,我说:“难道不让你搭车的,都不是好心人吗?你这样等车,不是浪费时间吗?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,也没有免费的便车。你可以不付费用,我也不想收你车费,但是让我瞧不起你!”我那话说得有点重,那个旅友心态极好,毫不在乎,一直在谢,走了很远还向我挥手。
我反对以乞讨的方式进行旅游,就像谷某和刘某那样。要饭是乞讨,蹭车一样是乞讨,除非你是和尚化缘,否则绝无尊严。为了达到蹭车的目的,满脸堆笑,低三下四,上车之后,还要不断的与司机套近乎,都是废话,赞美的话有些肉麻。
更何况,你们有钱,把自己的钱留起来,占别人的便宜,可以心安理得,这是什么人品?“不占别人便宜”,这应该是三岁幼儿就知道的品德,谷某刘某等人却以占便宜为荣,真是无法理解。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,有一农民回家,买不起火车票,他就徒步行走;有一大学生没钱买票回家,他就骑自行车行走……他们傻吗?不是,他们有道德底线。
一个不怎么善良的人,去考验别人的善良。同意搭车的就是好人,不同意的肯定不是好人,什么逻辑!有个深圳人,不带钱出门,一路上借钱,考验别人对他的信任,真是可笑之至;还有年轻女子因为蹭车,把命搭上了……如果你吃完饭,你让旁边不认识的顾客帮你买单,你觉得合适吗?肯定招来一顿爆揍!如果大家都像谷某和刘某这么聪明,满世界蹭车,那我们的社会岂不是乱了套了!
旅游,尽量把我们的善良传递给这个世界,而不是考验这个世界,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
扇子
□刘学友
京城已进入六月,天气热得就像蒸笼,待在屋里,门窗都打开了,仍然热得难受。我忽然看到母亲的床上有一把扇子,这把扇子是竹皮做的,久违的扇子我又看到了。
记得小时候,盛夏时节,母亲总喜欢到房荫下,坐在椅子上,拿着一把芭蕉扇呼扇呼扇地乘凉。那时芭蕉扇很盛行,几乎家家都有几把,扇起来风很大,把衣角都能扇起,你出了一身汗,扇几下芭蕉扇,感到一阵阵凉风侵入你的肌骨里,心平静了,没了急躁,得到了一种享受。我对芭蕉扇还有格外的情感,它能使我联想到那茂盛的芭蕉林。我生在北方,没有见过热带郁郁葱葱的芭蕉林,但冬天里窗户上结的冰花,那像芭蕉林似的冰花是屡见不鲜了。芭蕉林对于我有了直观感受,再看看手里的芭蕉扇,每片叶子都那么大,它干了折叠后还那么大,若是绿色的、鲜活的,会像一顶伞撑在你的头上。
纸扇一出现大约就是以一种工艺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,纸扇上画着各种图案:山水、花鸟居多;也有各种各样的盆景。“文革”期间,纸扇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,那也是以美术书法的形式写上的。纸扇可以折叠,携带方便,又美观,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。大街小巷,特别是在影院里,年轻人拿着纸扇已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后来纸扇越做越别致,越做越灵巧,变成了真正的工艺品,起不到扇风的作用,价钱又贵,它便失去了使用价值,而只好摆在了工艺品柜台上供外国旅游者采风了。
社会的进步,电扇、空调进入了千家万户。古老的芭蕉扇、精美的纸扇,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了。有时在电视中看到围棋高手对弈,中国棋手喜欢拿出一把纸扇,作为一种装饰、玩物在悠闲地摆弄着。而芭蕉扇在老人手中也消失得不见了踪影。
一个时代,有一个时代的事物,芭蕉扇的时代已经像敦煌石窟一样离我们太遥远了……